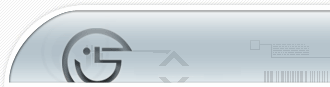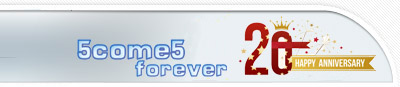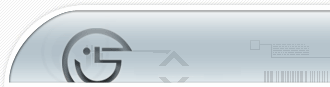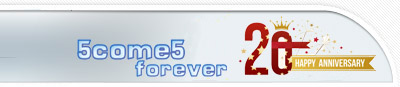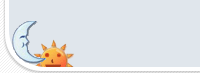我想起的是一辆车和它的车轮、引擎、方向盘,还有油箱。
一百多[屏蔽],这辆车的形象是一架吱吱作响的老马车;腐朽的木制的车轮,缰绳套住的马承担着引擎、方向盘和油箱的责任。弓着腰甩着鞭子的驾车人,扮演着最后的[屏蔽]者。在厚重的沉淀着血腥与文明的古老驿道上,缓缓而行,残阳如血的余光里,驾车人瘦削而弯曲的脊背,凝结成一幅象征苦难与忍耐的雕像。
历史在那一瞬间断裂了,断裂成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倒映着圆明园的火光和一个辉煌旧梦陨落时的最后光芒。终于,由于历经了太长太长的历史,染上了太多太多的风雨,老马车陷入了时间的泥潭,再也不能够移动。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时刻。
五六十年后,老马车进化成了一辆黄包车,车轮仍然是木制的。而方向盘引擎和油箱的角色由一个身着短衫,脖子上挂着汗巾的目光呆滞的汉子来充当。在旧上海的灯火辉煌和歌舞升平中,他一步步丈量着大上海的繁华与落寞。于是,出现了一个名叫骆驼祥子的车夫,他的被黄包车一一剥蚀的强壮的身体和淳朴的灵魂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最终,黄包车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没落和一种罪恶的延续,走进了历史的死角。它再也无力拉动这个堕落的城市。制约它的,不仅仅是速度。
历史之河在静静地流淌,它流过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流过一条道路又一条道路。
苦难像河流一样漫长,黑暗像囚笼一样牢固,时间凝固了。形形[屏蔽]的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社会的脚步在徘徊中彷徨,在彷徨中张望。它在重新等待一辆车,一辆有方向盘,有车轮,有引擎,还有油箱的车。一辆完整的车。
终于,有一天,车来了!它驰骋在高速路上的速度是一场变革,一场惊天动地,劈山破岩的变革。它发动的引擎的声音是时代变迁的最强有力的心跳,它紧握的方向盘转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它急驰的车轮象征着忠诚和永不出轨的承诺;还有默言的油箱,是车运行的血液。
车实现了它的飞越,社会变成了一架有条不絮、高速旋转的机器。

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孙紫琳 欢迎进入我的博客
http://xiayx.blogcn.com[ 此贴被相约普罗旺斯在2006-10-08 15:39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