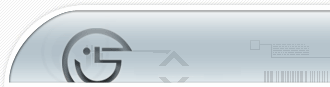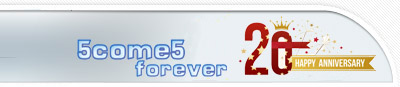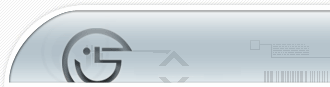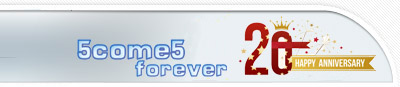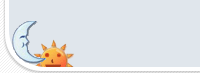Quote:
引用第726楼小白菜于2007-01-15 13:25发表的:
我把校报拿了一份
那篇东西被改了好多,本来就写得烂,改了就更烂了。
另外两个有意思的地方: 苏坦舍幻娜
三等奖:《咱们学校》 李恒
说句实话,其实那篇本来就不怎么样,没有你另外一些小说啊,童话什么的好看,可她就喜欢这个调调~有一些是我改的……
如下:
错身而过的岁月
小白菜
* * *
1996年秋天,爷爷去世了。
最后一次看到爷爷,是在四伯家中的大床上,那时候爸爸和几个伯伯一起围着那张床,脸上都是悲伤的颜色。我的心理有些畏惧,我慢慢的走近床前,看到爷爷安静的躺在那里,头发和胡子还是那样花白花白的。爸爸在一旁轻轻的对我说:“宏娃,快喊爷爷。”
“爷爷!爷爷!……”
在做法事的和尚为爷爷念安魂经的时候,我和几个哥哥一起跪在爸爸和伯伯的后面,伯伯头上都戴着孝,而我们只是手臂上缝上了一块黑色的孝。我不敢抬头,心里在想爷爷死了过后灵魂到哪里去了呢。爸爸常说在杜家,爷爷的书法是无人能及的,可爷爷的灵魂也会写毛笔字吗?
“宏娃,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爷爷手把手教你写毛笔字,那时候,你毛笔都捏不稳。”在许多年以后,爸爸还常常这样问我。可是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我还太小,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六岁那年爷爷到我们家里来时,我把刚写好的一篇字拿给他看的情景。
“你这个字没有力气,我写几个字给你看。”爷爷没有象爸爸通常所做的那样夸奖我,这让我感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爷爷走了过后,我还向爸爸争论:“其实爷爷这几个字写得还没有我整齐。”
三岁的小侄子在和尚念安魂经的时候突然站了起来,被[屏蔽][屏蔽]一下子抓住,一个巴掌打到了屁股上。“哇!”小侄子一哭,整个屋子里气氛更加悲伤,我看到伯伯和爸爸都在用手背抹着眼泪,而妈妈和伯娘们都已经哭出声来。
* * *
爷爷下葬那天天气很冷,和尚在前面扔纸钱,纸钱扔到空中被风吹得纷纷扬扬的很好看,伯伯则一路放着鞭炮,声音在田埂上跌跌撞撞,干涩而冷清。到了被选作坟的那块田上,前面是几个哥哥几天前挖好的一个大坑,很大,不过还是没有四伯家里那张木床大。爷爷以前一直睡在那张木床上。
“军哥,你们挖坑做什么呢?”那天我把一块土扔到军哥头上,问他。
“范宏你个死娃子,”他把头发上的土拍干净,“我们挖个坑好让你爷爷睡觉。”
“我们家里不是有床吗?为什么还要爷爷睡到田里面呢?”
军哥一下子被逗笑了,“人死了就要睡地下,我们还要烧钱给老人用,老人好保佑我们升官发财。”我看着眼前那个大坑,心想人死了真好,不用象爸爸那样拼命赚钱,直接有人给你送来。于是我指着这个坑对军哥说:“我也想睡到这个里面。”没想到军哥表情一下严肃了,他放下锄头从坑里爬了上来,从旁边一个装供品的碟子中撕下一点点碎馒头在我头顶上绕了一圈,扔进了坑里。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锣和唢呐声一下子响得更大了,大伯点燃了一串长长的鞭炮,我看到红色的火炮四下纷飞,青烟从刚盖好的土上弥漫开去。
后来每年清明节爸爸都会带着我来到这里,为爷爷烧纸、敬酒、作揖。在前年爸爸一边烧纸一边说:“爸,您孙子还是有这么争气,今年考了个重点,你保佑他以后平安幸福。”我则在一旁一边笨拙的作揖,一边静静的听着,眼睛有些湿润。
* * *
那天晚上,我在四伯家和军哥一起睡,有很多客人还没有走在楼下打麻将,我躺在床上也丝毫没有睡意。军哥叫我讲一下现在喜欢的人,当时我喜欢一个刚转过来的女生,但那个人似乎有些冷漠,于是我也会为此有些孩子气的烦恼。我们聊了很久,后来他爬起来翻出一张照片给我,问我照片里面那个女孩怎么样。
当时自己心里早已容不下其他女孩,我问他这是他喜欢的女生吗,他说他喜欢的人比她还要丑一点,我很不客气的表示感叹:“这个女的本来就不好看,那个人比她还丑?”我记得当时军哥楞了一下,脸上表情有些复杂,可是当时自己并不在意。两年过后,军哥辍学了,那时侯他刚上完初中,而我也正好小学毕业。
又过了几年,军哥结婚了。那时侯我已经知道照片上那个女的,就是军哥初中一直喜欢的女孩,可是后来她上高中去了。我现在很后悔那时侯所说的那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对军哥造成了伤害。
军哥的妻子是媒人介绍过gate的,有点黑,并不漂亮,有着农村女人共有的自私和多言。我记得办喜事那天,军哥穿着专gate订做的一套西装,笑脸吟吟的到处招呼着客人。他对我还是象以前那样热情,可我知道今后我们将不可避免的走向陌生了。
不再有人为我用泥巴做一辆小车,不再有人会用铁丝和弹簧做一把火药枪给我,不再有人会在睡觉时捏着我的鼻子把我弄醒了,而同时,我也不再需要这些了。
再后来,军哥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外出打工,挑上了全家的重担,去年他的孩子出生了。而我则在大学中浑噩度日。过年时我们也许还能见上几面,可彼此已经没有更多的话。
* * *
爷爷去世后,爸爸依然逼着我每天写两篇毛笔字,一张一张的贴满了整面墙壁。每次回到老家还能在四伯家里看到爷爷写的“家和事兴”四个字,直到去年军哥有了儿子,四伯拆掉老屋盖了新房,那些痕迹才全部被时间所抹掉。
爷爷的坟上长满了荒草,我每次作揖的时候,动作依旧笨拙。爷爷留在我脑海中的一些印象也开始模糊融化,我的记忆从1996年开始清晰,可时间又将蚀掉那一年所留下的全部记忆。